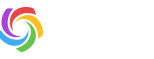

从益西老人家看到的松巴山,山顶就是原堡塞或寺庙遗迹
《隋书》和唐玄奘所记载的女儿国苏毗,很有可能就在拉萨以北的林周县。这里的松巴山上至今还有古老城堡的遗迹和吐蕃时代墓葬的依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称自己为“松巴人”,而松巴就是古书中的“苏毗”女儿国。
《西游记》里“女儿国”的故事,并非吴承恩完全杜撰,在青藏高原就有原型,而且“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过。这个女儿国的大体方位在哪里,当时的统治中心在何处,截止目前仍无定论。
不过有一种影响颇大的说法,认为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所攻灭的雅鲁藏布江以北的“森波杰”,就是汉文史书上所记载的“苏毗”亦即历史上的“女儿国”。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这个“森波杰”的最后堡垒“宇那堡寨”,就在被囊日松赞改名“澎波”而至今仍叫此名的拉萨市林周县。
在这里我们寻访到了一个“松巴村”(“松巴”是藏文“苏毗”的另一种汉译),这里有一个“松巴家族”,村后的“松巴山”上还有未知是堡寨抑或是寺庙的遗址,特别是在松巴山遗址西侧山腰和坡脚,还有当地人称为“松巴墓地”的一片墓地群,颇有一点藏王墓与列山古墓的气势。要知道,藏地的大型土葬墓,一般都是吐蕃及其以前的,此后慢慢就只有天葬了。如果说山顶的遗址还不能确定那是属于吐蕃时代的堡寨、还是吐蕃之后的寺庙,这大片的墓地,起码清楚表明了这一带在吐蕃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统治中心,因此很可能就是史料所记载的“女儿国”的都城。
1.史书记载,苏毗的臣子与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吐蕃互通声气,摧毁了曾经横跨昌都到阿里的苏毗古国
在藏地工作的一大乐趣,就是在工作之余,可以一边读西藏历史,一边“按图索骥”寻访历史书所讲述故事的发生地。尽管历史人物不会穿越重现,但那遗址也足以让人发思古之幽情,静静地凭吊一番。这是我一直坚持“周末一游”的缘由。
比如,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在当时人们所记的“赞普传记”中,记载了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塞”与父亲“囊日松赞”,怎样与雅鲁藏布江以北邦国的反叛臣子秘密联合,最后带精兵万人过江消灭敌手,将吐蕃领地扩大到雅江以北、最终奠定了吐蕃一统青藏高原的根基。
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当时雅江以南,已大部归于吐蕃(雅隆部落)治下,都城在秦瓦达孜城堡(今山南琼结县)。但在雅江以北,主要有两位统治者,一位称为“森波杰达甲吾”,一位称为“森波杰赤邦松”。这两位统治者势力不小,就连当时的吐蕃赞普达日年塞,也得把自己的妹妹“嫁在森波杰之侧”。可能因为势力强大,据说这达甲吾“背离风俗,改变国政,恣意妄为”,谁劝谏就处罚谁。
有一位达甲吾的旧臣,可能资格比较老,名叫“念·几松那保”[2],大胆地指责达甲吾“嗜恶反常”、“风习日乱”,被达甲吾逐出大臣之列。几松心怀愤恨,居然杀死达甲吾,归降赤邦松。至此,雅江以北也出现了一位唯一的统治者。
赤松邦赏给几松许多土地和奴户。其中有“娘”与“孟”两氏——吐蕃之前的所谓“小邦时期”,通常是把被降服的部落或氏族整体变为奴隶(奴户),这里就是指娘氏与孟氏变成了念氏的奴户。不知是不是有点小人得志,或是由于以往有积怨,念氏的主妇即“女当家人”巴曹氏对奴户很粗暴,经常威吓,“且以妇女阴部辱咒之”——据说这是藏地至今犹存的最毒的咒辱!
娘氏不堪忍受,跑到赤邦松那里诉苦。赤邦松却说:“没有人比念氏更忠于我,主妇辱咒呵责,示以女阴,对你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娘氏极为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在此前后,赤邦松的一位似为主管监察的官员“韦·雪多日库古”与代理内相“辛·墀热顿孔”因事在一湖边格斗,辛氏竟将韦氏杀死了。韦的兄弟名叫“旁多热义策”的,到赤邦杰跟前鸣冤,要求赔偿抵命。赤邦松则说:“辛·墀热是代理内相,我不好说他。况且以善诛不善,诛则诛矣,何用抵偿?”韦氏也极为愤怒。
这一个奴户、一个官员,因深恨赤邦松,不约而同走在一起,萌生了反叛赤邦松、归降吐蕃之意。此后,韦氏的舅氏一族“农氏”以及与娘氏关系密切的蔡邦氏也加入进来,偷偷与达日年塞联系并立盟誓——吐蕃前后的人们很相信盟誓的威力,许多事情都要靠盟誓定下来。但不久因达日年塞去世,事情就暂时耽搁下来。
达日年塞之子伦赞赞普继位后,再次与赤邦松的这些叛臣们盟誓,并约好里应外合,攻打赤邦松。这之后,经过准备,伦赞赞普让弟弟伦果尔和母后守国,他亲率“精兵万人”,“启程远征”。娘氏与农氏充当耳目,韦氏与蔡邦氏充当向导,“遇大河于渡口涉渡,仔细查明行军道路”,最终攻破宇那堡寨,灭掉了赤邦松,王子“芒波杰孙波”(意为“(土地)众多的苏毗之子”)逃亡突厥。至此,雅江两岸尽归吐蕃,伦赞赞普将赤邦松的领地“岩波”(似意为“沟坎”)改名为“澎波”(意为“富裕”),韦氏以及岩波之地的民众,则因他“政比天高、盔(权势)比山坚”,而尊称他为“囊日松赞”(意为“天山赞普”)。娘氏、韦氏、蔡邦氏等,因功获得大片土地与奴户,以后就成为吐蕃王朝时期的显赫家族,有的屡屡与王室通婚,有的氏族成员时任论相。
囊日松赞攻灭赤邦松,的确是吐蕃历史上意义极为重大和引人注目的事件。不仅是这一战,使原先僻处于雅江以南、因喜马拉雅阻隔而无法向南发展的吐蕃,重心移到江北,控制了藏地最为重要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两岸肥沃的土地,从而方便北上西进,最终在松赞干布时期,定都拉萨,攻城略地,很快降服藏地其他区域的大小邦国,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而且,这一战争的另一方,还与藏地最有传奇色彩的“女儿国”有关。
2.被灭亡的苏毗国,原来就是唐僧曾记录的女儿国?
在汉地史书中,苏毗是一个传奇的“女儿国”。《隋书·女国传》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子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其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中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
有趣的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了这个“女儿国”——吴承恩所写《西游记》中的“女儿国”,部分就渊源于此:“此国(北印度)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孥瞿钽罗国(原注:唐言金氏)。出上黄金,因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为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牛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今新疆和田),西接三波诃国(今拉达克)。”——尽管玄奘并没有提到这女王“姓苏毗”,而称该国为“金国”(与《隋书》所说女王丈夫号称“金聚”相符),但从他的文字描述看,显然与《隋书》所说的女儿国或者说“苏毗”,是一回事。
按史料的可靠性讲,《隋书》比玄奘所载更为权威一些。因史载这个姓苏毗的女国于“隋开皇六年”(586年)曾“遣使朝贡”,与隋朝有直接交往,因此《隋书》对苏毗女国的详细记载,有些很可能来自于使者的介绍。玄奘的记述虽然来自于传闻,但也离事实不远,因他所描述的“北接于阗”,得到了考古的证实。在今新疆和田市民丰县(历史上也属于阗)的尼雅遗址,发现了许多大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的文字资料,其中有20多件,都提到了当地受到“苏毗人”的攻击。而其所记苏毗“东西长,南北狭”,正可与《隋书》所言苏毗向天竺贩盐,并与天竺(在极西)和党项(在极东)都有战争相符,说明它是一个横跨藏北地区(藏北多盐)的部落联盟(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所以,从数量不多的史料可以推知,经过激烈的兼并,尽管藏地仍有一些小邦——比如不见于十二小邦名单上的洛扎,还曾打败过达日年塞,并把他囚禁起来——但在藏地,当时已大体形成了最大的三股势力,一是阿里的象雄,二是雅江以南的吐蕃,三是雅江以北的苏毗。根据相关史料,当时苏毗所控制的地域(不能理解为像后来的国家那样严格统治,而只是形式上有一个统治中心的部落联盟),西在圣湖玛旁雍错附近与象雄相接,东与今昌都及四川西部的附国接壤,北在唐古拉山南北与突厥相邻,南隔雅江与吐蕃为界。
不过,到了达日年塞时期,雅江以北的苏毗内部,已是矛盾重重。当时苏毗有两王(这与《隋书》记载相符,两位王均称为“森波杰”,说明是同属一个国度或部落联盟)。
有一种看法认为,身为“大王”的森波杰达甲吾,很可能想结束“两王共治”、氏族及部落参政的传统做法,树立相对专制的王权,因此与赤邦松以及旧氏族首领的矛盾日深。所以吐蕃史料记载达甲吾的罪行是“背离风俗,改变国政,恣意妄为”,大臣念氏指责达甲吾的不是“腐化”、“奢靡”,而是说达甲吾,“嗜恶反常”、“风习日乱”,显然是说达甲吾不守旧规矩。这时“小王”赤邦杰想必也有独裁之心,所以在念氏杀死达甲吾之后,赤邦松就欣然当上了整个部落联盟的唯一主人——达甲吾被臣子杀死,居然没有引起动乱和战争,就一切均归赤邦松,说明这两位森波杰应是大小王的关系,大王死去,小王继任,理所应当,所以才如此平静,而不像吐蕃赞普来夺王位,要“精兵万人”才得成功。史载囊日松赞还一直打到藏北,藏北多野生动物,囊日松赞因打猎获得的动物肉太多,拖到地上沾上了藏北多见的盐巴(苏毗常以贩盐为利),这才发现了食盐的美味,表明王弟与母后监国、“启程远征”并非小题大做,极有可能囊日松赞是在攻下宇那堡寨后,又一路追击苏毗王子,才打到了藏北地区。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苏毗的最后堡垒“宇那堡寨”,才是苏毗真正的都城。那么,它又是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3. 拉萨以北的林周县,苏毗人的后裔依然在此繁衍
从囊日松赞攻下宇那堡寨后,把原先的“岩波”改为“澎波”,说明它即位于原先的岩波、后来的澎波境内,也就是今天的林周地区。所以在得到一本《林周县志》后,我就开始注意翻查有关“宇那堡寨”的信息。果然,在县志中,记载有“今林周境内有‘额布查松’邦国,王名公赤森波杰赤邦松,辖区中心在今江热夏乡斯木巴村一带,有城堡遗址”。见此,我大喜过望,还有城堡遗址,那就好找多了。
然而,托人在林周县打听这城堡遗址的具体地址,结果很令人意外:不仅遗址不知在何处,就连“斯木巴村”人家也没有听说过!这是怎么回事?我反复琢磨这“斯木巴”是哪几个藏文字,一边念叨着“斯木巴、斯木巴……”,突然恍然大悟,这“斯木巴”,应该就是“孙波”或“森波”了。于是忙让县里的人,寻找发音类似于“孙波”或“森巴”之类的地方。很快,县里回复了:有一个叫做“松巴”的自然村,现在一般称为“农牧处组”的,附近山上有遗址。
于是我们驱车前往。这个村民组属于今天的林周县江热夏乡江热夏村,位于澎波河与拉萨河的交汇处,周围是绿意盎然的广袤原野,真当得起“澎波”(富裕)之名。“江热夏”意为“东柳园”,附近果然绿树成荫,令人不禁联想起有关苏毗崇拜“树神”的传说。
在村里找到了一位现年71岁的老人“益西索朗”。据县里同志介绍,他算是村里有点文化、很有见识的人了,但问到有关“苏毗”或“孙波”历史的事,他一无所知。不过,一提起“孙波”这个名称,老人却一脸骄傲的表情。原来,这个自然村的40多户,都属于“孙波”家族——老人的读音更接近于“松巴”。村子背后的山,就叫做“松巴”山,海拔近5000米。据老人讲,山上有许多类似于城堡又像寺庙的旧址,60多年前,他们全家就住在松巴山顶。现在,生活在半山腰的叫“上松巴人家”,生活在山脚下的,是“下松巴人家”,但山上山下的都属于一个家族,而老人就是这个“松巴家族”的族长!。——这一上一下,也不禁让人联想起苏毗或曾分为农业区和游牧区、但同属一个苏毗的史实。
老人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村里的“驱雹巫师”。驱雹巫师藏语称“阿巴”(本义为“咒师”),源于原始苯教的巫师。在原始部落和氏族时代,苯教巫师一般由氏族的长者和部落的首领来担任。在遥远的古代,掌握了神权,等于能通天、通神,就可以牢牢掌握和控制氏族与部落大权,因此,苯教巫师在藏族先民心目中,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苯教产生于西部象雄,但吐蕃的苯教,主要是在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时期,从苏毗流传过来的,故称“苏毗苯教”(或译“孙波苯教”)。——老人的这一特殊身份,就像松巴山上的遗址,让人难免联想起1400多年前,这个苯教国度的兴衰浮沉。
目前松巴山上的遗址,已很难寻觅到1400多年前的陈迹。据乡里人介绍,遗址现存房屋废址41座,佛塔5座,煨桑台1座,显然是一处寺院的遗址。寺院的来历及何时废弃的时间不祥。不过,藏地寺院除一些新创者外,有不少往往建立在古代的一些堡寨遗址上。因为古代藏地寺院不只是简单的宗教场所,往往是一个地方文化、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中心,所以在兵荒马乱的古代藏地,寺院往往也需要建在易守难攻之处,与堡寨的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松巴山上的遗址,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所有建筑都建在松巴山山顶及两侧陡峭的坡地上,在建筑四周依山势建有围墙九段,围墙与悬崖峭壁在建筑外围共同形成了一道屏障。
可以想见,在森波杰的时代,高大的堡寨(甚至可能有九层),像吐蕃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一样,巍然耸立在松巴山顶(《隋书》所谓“山上为城”),俯瞰着蜿蜒南去的拉萨河支流澎波曲,还有河流两岸大片的绿色农田。彩色涂面的男人们在农田里耕作,女王与数百女官,处理着近到旧堡辗噶尔,远到拉萨河源头更北地区的辽阔草原上各部落的事物,包括与远到西方的天竺、东方的党项之间的贸易(贩盐)有时是战争事务。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部落与氏族众多、统治松散的古老大国,这巨大的堡寨显得仍很渺小,加上各氏族、部落头领(包括境内的小邦王)对国家事务往往意见不一,女王对国家的管理深感力不从心。眼看着雅鲁藏布江南部、与苏毗有姻亲关系的吐蕃只有一个赞普、男人专权,往往更有效率,苏毗的统治者也感到了些许不安,甚至是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传闻东方新近出现了一个强盛大国,威名远震(隋朝初年隋文帝攻打突厥屡屡得胜),苏毗王室派使者与大国结交,或许隐含了引进外援以抗衡来自雅江南岸吐蕃威胁的意图——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9年)苏毗朝贡时,正是后来密谋要攻灭苏毗的吐蕃赞普达日年塞当政时期,这或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巧合。
与此同时,苏毗的“一把手”达甲吾,也企图仿照吐蕃赞普的做法,让自己的权力更集中,然而不久就因此覆亡了。小王赤邦松的想法其实与达甲吾一样,也要加强自己的权威,因此不理会奴户娘氏的抱怨,反而为忠于自己的念氏辩护。娘氏家族那时的领地,一般认为是靠近热振一带,那是拉萨河的中游地区。再向北,就是苏毗的游牧部落了——后来吐蕃王朝划定苏毗茹,南部界限就在拉萨河源头的麦地卡。所以与游牧部落邻近的娘氏,与北部苏毗各部,关系一定也很密切,甚至在对赤邦松不满方面,还有不少共同语言,这或许就是后来苏毗反叛吐蕃时,已成为吐蕃宠臣的娘氏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就将苏毗北部各部落平服的原因。当然这是后话。另一方面,赤邦松又因袒护杀了人的“代理内相”(可能是新近提拔、比较听话的宠臣),而得罪了邻近吐蕃的韦氏(韦氏所属的“卧域”,在雅江北岸,今山南桑日县的雅江北部地区),终于引来了吐蕃的大兵。
不知在怎样惨烈的战火中,松巴山上的这座“宇那堡寨”被攻破,甚或被夷平——因为吐蕃赞普并没有在澎波这里建立宫堡,而是在与澎域有一段距离的拉萨河对岸的一条山谷“甲玛沟”,兴建了“强巴弥居林”宫,作为吐蕃统治雅江以北地区的大本营。此后,宇那堡寨就慢慢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被多数藏地人所遗忘,仅仅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好在还有一批“松巴人”,从吐蕃时期,一直到藏地混乱时期,看着这里兴建起寺庙,又默默注视着寺庙的坍塌,他们都坚守在这废弃的堡寨遗址边上。花开花落、云起云消,时代在变,风俗习惯也在变,那些“女子当家”的传统早已销声匿迹,但“松巴”的名号一直没有改变,似乎在等待着世人重新审视这座“女儿国”的都城。